甘为科学作“五毛”
——写在《海与人》再版之前
“五毛”这个词不知道是哪年出现的,开始它被用来讽刺支持当局的人及其观点,后来这个词的含义逐渐泛化,连粉丝去追捧一个歌星也会被称为“五毛”。
总之,凡是对某事物积极提倡和鼓励,并且努力批判质疑它的观点,类似行为都可以称为“五毛”。按照这样的用法,我就是一个科学事业的“五毛党”,并且甘之如怡。而《海与人》,就是一部旗帜鲜明的“科学五毛小说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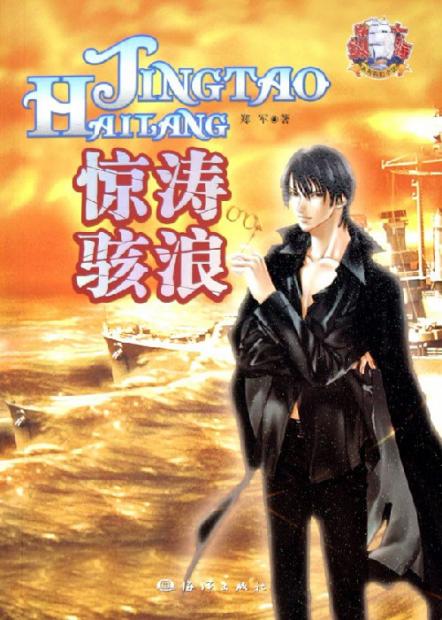
《海与人》创作于2004年,距离我写处女长篇《时代之舱》已经过去了五年。《时代之舱》是在激情支配下完成的创作。那时候我对于种种反科学观点十分不理解,觉得他们非疯即骗。这些人是不是要沽名钓誉啊?没有科学,你们还不知道在哪片山沟里种地呢。
到了创作《海与人》的时候,我不仅接触了更多反科学的观点,还接触过现实中的一些代表人物。座谈会上,餐桌上,正式观点,私下言论,都接触了不少。越多地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程度之高和态度之真诚,也越能体会反科学观点远不是那么简单,更无法象扫地一样扫干净。
我明白,在众多文化层次如此之高的人站出来反对科学的今天,如何宣传科学对我来说是个复杂得多的任务,那种非黑即白的写法完全不行了。
《海与人》成为我以“反反科学”为主题的第一次尝试。它集中描写了诸多反科学观点中的一种——生态中心主义。当然,小说里写的只是我当时理解的生态主义。北师大的田松看完这部小说就指出我写错了,反面人物仍然是“人类中心主义者”,离真正的生态中心主义还差得远,不过情节已经无法改写,况且我当时也无法完全进入生态中心主义者的语境,真那么去写更写得不象,便只好将错就错。今天再版时,我也没有修改这一错误,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岂不更好。我尝试着在另外的作品里去更逼真地描写生态中心主义。
象我绝大部分作品一样,这部小说里没有“坏人”,也就是单纯损人利己的人。我觉得生活中这类人只能混迹于最底层,那些掌握高新科技的精英和街头混混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。他们里面不会出现“坏人”,但会有一些因持偏执信念而做坏事的人,这成为后来我的科幻小说的母题。
《海与人》第一次出版后,便有一位中文系教师来信说我写的是“复调小说”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文学概念,查过以后深以为然。是的,不光是这部小说,我的几乎所有小说里的反面人物全部有着远大理想,我必须先尝试解读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理想,再写出相应的行为,否则这些人物就成了脸谱。
令我兴奋的是,就在我创作海与人的同一年,我崇拜的前辈迈克尔·克莱顿完成了类似主题的长篇科幻《恐惧状态》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他的《未来世界》和《侏罗纪公园》,但就是中国的科幻迷都很少有人知道《恐惧状态》这部晚年作品。
《恐惧状态》写了这样一个故事:全球变暖完全是谎言,是阴谋家雇用一些专业科学家制造的骗局,其目标是为了让全球那些不懂科学的人处在恐惧状态中,以实现他们的某些目标。为了阻止这个谎言被揭穿,他们不惜杀人害命。
在今天,这个主题几乎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,完全是政治不正确。人们更喜欢他的《未来世界》和《侏罗纪公园》。你瞧,在这些作品里,科学闯了祸,科学家干了坏事。这样写才爽。克莱顿不仅在《恐惧状态》里亮明自己的观点,而且还充满激情地揭穿一些与情节无关的谎言——物种大规模灭绝、滴滴涕的危害、电磁辐射致癌等。说实话,如此尖锐地站在反科学潮流之对立面,如此鲜明地为科学进步讲话,我现在还不敢这样做。也许再过些年,再多一些知识和经验,我也能有象他那样的勇气吧。
科幻前辈刘兴诗老师坚持认为科幻应该反映现实,我也认为必须如此。而且我进一步认为,科幻应该反映的是与科技进步有关的现实,毕竟描写其它领域的现实,科幻不如其它类型小说更擅长。
在《海与人》中,我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现实—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大型科技项目的增加,中国将成为全球生态主义者的首要攻击目标。他们以前反美国,反日本,还曾经被法国人炸掉一条船,以后他们和中国的冲突绝对不会比那些更缓和,如果不是更激烈的话。
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,但它正向我们走来,长则十年八年,短的话甚至会与《海与人》的再版一起让大家耳闻目睹。如果这本小说能在这方面给中国人提个醒,那么它的一个很实际的目标就达到了。
科幻干预现实?是的,它先要能干预和科学进步有关的现实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