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格决定命运,这是主流文学千古焠练出来的金科玉律。一部叙事作品的基本矛盾来自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,直到今天,作家和编剧们在创作之间都得先设计好主要人物的性格。
只有在幻想类文学兴旺发达后,人们才能换个角度看待这个创作规律。性格之所那么重要,是因为所有现实题材的故事只能在一个背景下展开。这是背景就是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。
相当一部分幻想类文学的特色,就是给出一个迥异于现实和历史的背景。而同样长篇幅里,给环境留下的笔墨多,给人物留下的笔墨就少。以科幻小说的伟大先驱《格列佛游记》为例。当主人公来到大人国、小人国时,单是身体尺度方面的差异就构造出许多情节。格列佛本人的性格模糊不清,那些形形色色的海外异国里,也没有多少鲜明的人物形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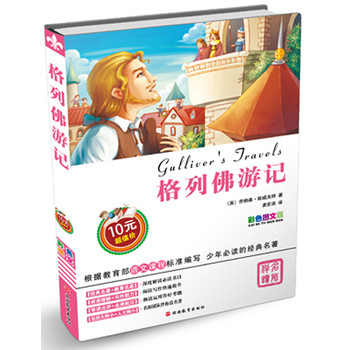
19世纪科幻文学大批量产生后,早期作家并没有象斯威夫特那样天马行空,基本都把背景放在当时当地,描写一个科学怪人在陋巷密室里搞发明。故事环境作者和读者都熟悉。
凡尔纳是科幻文学的转折点,他一点点把故事背景扩展到现实生活之外。先是非洲,美洲那些有人居住,但欧洲人很少到达的地方,后是深海、天空、地下、月球这些当时人类还到达不了的地方。晚年的凡尔纳已经把故事写到了太阳系,或者未来。

凡尔纳谢幕时,科幻可以写架空背景已经成为共识。伯勒斯和威尔斯这些顶梁柱,都以描写异域为能事。进入20世纪,科学发展给科幻作家新的启发,创作出外星世界、平行空间、虚拟世界、时间旅游等超现实的背景。
然而,也就是从凡尔纳开始,环境便压倒人物,成为科幻作家重点描写的对象。读者想看的也是不同于现实的怪异环境,不怎么关注人物性格。甚至,有些当时的代表作如《回顾》,连情节都被淡化,作者大段大段描写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。主人公成了新异环境的见证人,完全不在乎自己被抛到一个陌生环境后会有什么遭遇,该怎么应对。
这种写法也影响到中国早期的许多科幻作品。那里面的人物很少有行动,只是看到了这个,遇到了那个。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是这种写法的代表。作者想写的,读者要看的就是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,而不是人物做了什么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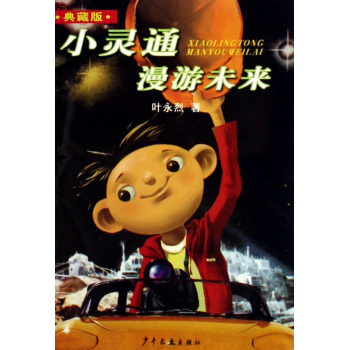
能写出许多奇妙的幻想世界,这是科幻小说的伟大贡献,但一条腿很长而另一条腿过短的话,终究不能顺利前进。上面那些作品其实是科幻文学刚刚出现,艺术形态还不完整时的代表作。怎么在幻想背景下把人写好,在环境描写和人物性格描写间取得平衡,这给了幻想类作家全新的要求。
全文发布于: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